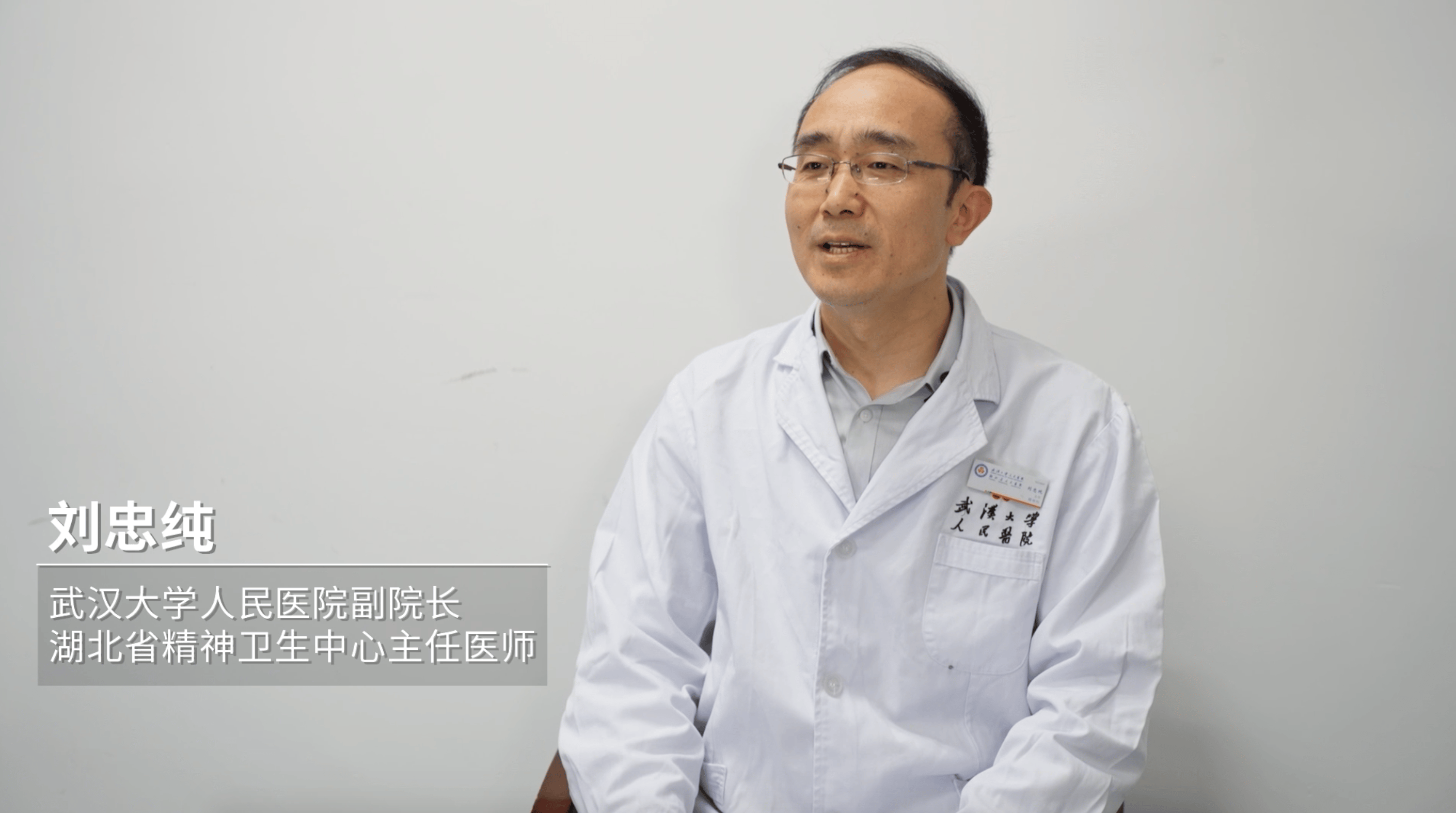“妈妈,我站在桥上站了很久了。我真的想跳下去,我真的不想活了。”
张昕没想到,接到这通电话后不久,女儿就在学校里吞药自杀。她站在ICU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才意识到自己对抑郁症的了解还是太少。
抑郁症也称抑郁障碍,是一种高发病、高复发及高致残的慢性精神疾病,几乎每个年龄段都有罹患的可能。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近十年来患者增速约为18%[1]。在我国,众多患者及其家庭也正经历着漫长的抵抗抑郁症之路。
▲ 微型纪录片《寻回快乐》
她这是生病了
一年半以前,张昕注意到了女儿的异常。寒假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但女儿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窗帘也一直紧闭。除了偶尔吃饭时起床,那段时间她甚至“懒”到不刷牙不洗脸。
张昕终于忍不住询问女儿到底怎么了,女儿突然嚎啕大哭:“妈,我想到了18岁就自杀。”那一刻张昕意识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
带着女儿到医院精神科就诊后,张昕从医生口中得知女儿现在正处于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状态中,需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抑郁症的临床表现非常复杂,心境或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以及快感缺失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精神心理卫生科主任医师马现仓介绍道,在抑郁症诊断时,核心症状至少要满足一条,而且至少持续两周以上。核心症状外,抑郁症还会影响睡眠、饮食和日常行为等,患者可能出现体重剧烈变化、全身疼痛不适、疲劳等躯体症状,以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和学习困难等认知功能变化。
![]()
像众多患者家属一样,得知女儿患抑郁症后,张昕的第一反应就是追问医生“为什么女儿会得这个病”。然而目前为止,抑郁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抑郁症是个人的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社会经历交互影响的结果。”马现仓说。
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让患者意识到,抑郁症是一种病,是需要规范治疗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精神科教授司天梅认为,虽然近年来抑郁话题越来越被大家关注,但人们对抑郁症还是存在一些误区。
目前我国抑郁障碍的临床诊疗现状并不理想,识别率、治疗率和充分治疗率分别为21%、9.5%和0.5%[2]。
在临床实践中,一些患者因为病耻感不愿承认自己患抑郁症,因为他们认为“得了这个病就像得了精神病”,也有很多表现为躯体症状的患者因就诊科室有误,容易误诊导致耽误了治疗。还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对抑郁症治疗怀着深深的恐惧,会将药物的不良反应与安全性划等号,怀疑药物是否具有成瘾性等。
“不愿、不知、不敢,这三种情况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庭中更为普遍。”司天梅说。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精神科教授司天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精神科教授司天梅
一条漫长的治疗之路
患了抑郁症的人,就像裹着一件湿棉袄在水里游泳。抵抗抑郁症之路,漫长而曲折。
最初,张昕只是带着女儿定期进行心理治疗。但女儿的情绪就像火药桶,可能前一秒很开心,后一秒因为某句话就会突然发怒,甚至有一些自残自伤行为。张昕不得不接受,女儿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必须服药的阶段”。
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后,张昕发现女儿的情绪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起伏再也不像过山车似的了,也没有了强烈的自杀、自伤行为。去年九月,女儿步入高中。那时,张昕以为一切终于柳暗花明。
但突然有一天,女儿无论如何说要休学。原来在全新的环境中,女儿整个人处于精神紧绷状态,无力学习也不和任何同学交朋友。在学校,她经常感到头痛、胸痛和心悸,课间她会躲到厕所里,全身发抖不敢出来。一天放学后,女儿在张昕面前大声哭喊“为什么逼着我上学”。
![]()
在临床中,张昕女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属于慢病,这就意味着对疾病的治疗和管理都将是长期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任何一种潜在症状和风险的忽视都有可能造成复发或者病情波动,许多患者在获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后就轻视了全程管理,也是导致抑郁症充分治疗率低的关键因素。而在最容易被忽视的临床表现中,快感缺失是最常见的一种。
临床上几乎高达70%的抑郁症患者经历过明显的快感缺失症状,不仅损害日常生活能力,还会损害认知,以至于很难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3]。此外,具有快感缺失的抑郁症患者病情更严重、自杀率更高[4]。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忠纯举例道,过去的临床治疗只关注患者情绪低落、想不想自杀的问题,经传统的抗抑郁药治疗一段时间后,患者的抑郁情绪缓解了,但却存在快感缺失症状,他会感觉“我好了我不想死了,但是活着既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愉快”。
![]()
但在治疗方面,过去常见的抗抑郁药物更多的疗效体现在减少负性情绪,但同时也会减少愉悦能力(正性情绪),加重快感缺失的症状。
为应对抑郁症日益严峻的形势,新靶点、安全性高等成为新药研发趋势。
在此背景下,阿戈美拉汀应运而生。目前,阿戈美拉汀已被推荐为抑郁症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5],且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从传统的三环类抗抑郁药,到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等基于单胺类神经递质的药物,再到阿戈美拉汀等靶点药物,药物发展在改善生物节律、睡眠节律,改善认知功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刘忠纯说。
在抗抑郁药物治疗的选择上要充分评估患者病情和自身特点,充分体现个体化原则,即每位患者的病情、治疗方案都不一样。同时,在抵抗抑郁的漫长时间中,需要综合治疗。“药物治疗外,抑郁症的治疗也包括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而配合治疗不仅指患者和家属要坚持遵医嘱,还包括让患者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调动自主性。”刘忠纯说。
共同托举
经过慎重考虑后,去年年底,张昕给女儿办理了休学,也根据医生建议开始调整治疗方案。今年3月,女儿主动提议要复学,甚至会开心地期待新的高中生活。节假日,她也开始约着朋友们外出游玩,像同龄孩子一样喜欢各种动漫角色。“我很期待孩子能够体验到幸福、快乐和安心。”张昕说。
对疾病认识不断深入,医学界对于抑郁症的治疗目标也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 70 年代,治疗有效是抑郁症治疗的目标。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症状改善和临床痊愈成为目标。“但近十余年来,随着患者需求的变化,现在我们的治疗目标是患者症状消失后,社会功能恢复正常,并能获得愉悦的体验。”刘忠纯强调道。
抑郁症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来自医疗、家庭和社会系统的支持,将共同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地面对生活,回归社会。
![]()
在2013年5月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后,十余年来,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在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下有了长足发展,抑郁症诊疗也从过去关注疾病本身到关注个体精神健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促进心理健康”作为15项专项行动之一,提出“2022年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20%和30%;焦虑障碍、抑郁症、失眠障碍患病率上升趋势减缓”等目标。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已有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5936家,与2010年相比,数量激增了205%。同时,全国精神科执业注册医生也增长至5万多人,比十年前增加了144%[6]。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我们仍需认识到,现有的精神卫生资源仍无法满足庞大的患者群体需求。仅以抑郁症为例,有关躯体化主诉抑郁症的比较研究显示,调查的抑郁症患者有37.1%首诊于综合医院[7], 所以加强精神专科医院建设外,还要加强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建设。”马现仓说。
除了在机构和人力资源上的投入,科研方面的突破也是关键。抑郁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如何找到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样的诊断标志物,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重点。近年来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分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不同疾病中的广泛应用,为进一步筛选抑郁症相关生物标志物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希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真正地去推动抑郁症在生物标志物方面的研究,指导临床诊断、预测抑郁症的治疗效果等。”刘忠纯说。
面对抑郁症的挑战,公众对疾病正确认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众多一线临床医生和专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专业建议和支持。
“要不断地进行科普教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改变对抑郁症的偏见和忽视。”为及时解答抑郁症患者对于疾病和治疗的疑问,也为给予公众精准、专业的科普教育,2018年司天梅携手科室一线的临床医生们,创办了抑郁症科普公众号“心晴指引”。六年来公众号陪伴无数患者和家属,成为他们随时寻求专业建议的渠道。在司天梅看来,这也是对“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院训的践行。
“我们应该正确地接纳这个疾病,鼓励抑郁症患者尽早地去接受专业的诊疗。要陪伴他,去倾听,这些帮助其实能让患者感受到‘我被理解了,我被接纳了’,让他们自己有希望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司天梅说。
随着对疾病的正视,在对抗抑郁症的漫长道路上,患者和家属也展现出更多的坚韧与勇敢。女儿生病后张昕意识到,家是孩子最后的港湾,她在前面遇到挫折时只能后退到家里。“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容器,去托住孩子,让她重新积攒能量后再出发。”
(文中张昕为化名)
参考资料:
1.世界卫生组织. (2022). 世界精神卫生报告: 向所有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转型, v-4. 世界卫生组织.
2.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study. Lancet Psychiatry. doi: 10.1016/S2215-0366(18)30511-X.
3.Mcintyre R S, Woldeyohannes H O, SoczynskaJ K, et al. Anhedonia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ults with MDD: results fromthe International Mood DisordersCollaborative Project[J]. CNS Spectr,2016,21(5):362-366.
4.Uher R, Perlis R H, HenigsbergN, et al. Depression symptom dimensions as predictors of antidepressanttreatment outcome: replicable evidencefor interest-activity symptoms[J]. Psychol Med,2012,42(5):967-980.
5.2015 年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
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http://www.nhc.gov.cn/xwzb/webcontroller.do?titleSeq=11451&gecstype=1
7.躯体化主诉抑郁症的比较研究ShanghaiArchivesofPsychiatry,2000,V01.12,No.2
作者:马萌
编辑:马敏
视频拍摄:白皓 张熠奇 梁嘉诚
视频剪辑:白皓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